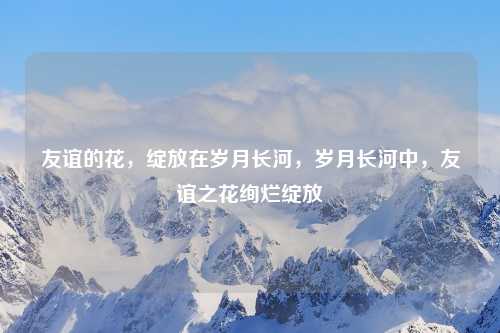冯友兰人生的境界,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精神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一个人的精神和思想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平均表现;精神境界分很多层次,有很多种说法不能一概而论,可以去看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之说;最高的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自古至今都有的返璞归真之说。
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重视学习环节。学习对我们精神境界的提升至关重要。学习的方法很多,内容也很多。学习贵在坚持,学习贵在恒心,学习贵在自知;通过学习,学会正确地思考、正确地判断、正确地洞悉;通过学习,不断拓展知识面,丰富精神生活,开阔思维视野,这都关乎精神境界的提升;注重实践历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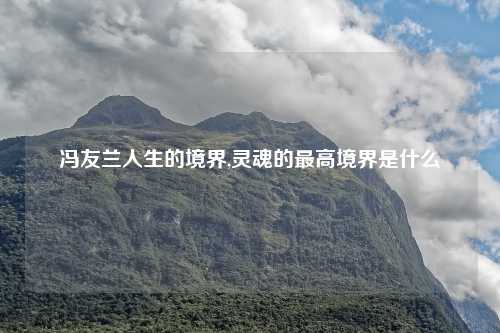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历练,包括学识能力、眼界心胸,思想观念,都需要不断修正,不断完善,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培养大爱情怀。精神境界除是复杂的精神要素的集合外,它还包含一定的情感要素。而是否具有大爱情怀,是一个人精神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有仁爱之心,爱国家、爱民族、爱集体、爱人人,这样我们做事就会处处考虑到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就会处处为别人着想,为学生着想,为子孙后代着想。
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
冯友兰
1895.12.4—1990.11.26
哲学家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
享誉海内外的学者
冯友兰先生,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公元1895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六日)生于唐河县祁仪镇祖父家中。1990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九十有五。
先生祖父讳玉文,字圣征,有诗集《梅村诗稿》。父讳台异,字树侯,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戊戌(公元1898年)进士。伯、叔父皆秀才,亦有诗集传世。冯氏有地千余亩,合族而居,家常二三十人,耕读传家,为当地著姓。先生母吴氏,讳清芝,通文墨,持教有方,曾任本县端本女学学监。
先生6岁即入家塾就读,先读《三字经》,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塾中亦授《地球韵言》一类新学,可谓新旧兼备。1904年,台异公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先生与弟、妹随母徙居武昌,由母监读《书经》、《易经》、《左传》。1907年,台异公知湖北崇阳县,举家至崇阳,先生随县教读师爷习古文、算术、作文。次年夏台异公病故于崇阳,先生乃随母返故里,仍在家塾就读。
1910年考人唐河县高等小学预科。次年,以第一名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转入武昌中华学校,是年冬应试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时中国公学以英文授课,先生尤感兴趣者,为耶方斯(Jevons)之《逻辑要义》,因立志习西方哲学。1915年夏自中国公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校后即改文科,因西方哲学门未开,遂入中国哲学门。不二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皆主教于北大,新文化运动颇盛一时。受此影响,先生对东西文化问题甚为关切。1918年夏于北京大学毕业,次年与友人响应五四运动,创办《心声》月刊,为当时河南宣传新文化之唯一刊物。同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冬,赴美国留学。
1920年1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院哲学系。先生在哥大师从杜威先生(John Dewey),其心志仍在中西文化比较,如是年冬在纽约访泰戈尔(Tagore),次年在哥大哲学系宣读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皆其例也。至先生作博士论文时,思想忽有变化,盖因先生在美研修西方哲学史,乃发现时人所说东方与中国思想特有者,要皆在西方古代亦有之。先生即以《天人损益论》为题,打破东西界限,将人类自古以来各种人生理想分派叙述之。后其中译本以《人生哲学》名题,列为高中教科书,流传甚广,颇有益于青年之教育。先生乃进而觉知,一般所谓中西之异,实际是古今之别,皆因西方已完成近代化所引起。故此后力主现代化不遗余力,以工业化为中国获民族自由之出路。先生在美时,官费常阙,因多赴餐馆做工,间亦至图书馆管理报纸,以谋生活。1923年夏,论文答辩通过,即取道加拿大归国,任中州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学系主任。次年,英文博士论文出版,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
先生1925年秋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年底应约北上,任燕京大学教授。先生自美返国后,志愿介绍、研究西方哲学,然在燕京受命开授“中国哲学史”,此一机缘竟对先生后来学术发展有莫大影响。1928年秋,以友人罗家伦之故,先生转至清华大学,为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仍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至30年代初,先生完成《中国哲学史》二册巨著。此书上起周秦,下至清季,钩玄提要,条分缕析,其义理解说,尤明白清晰。先生尝谓此书以“释古”为法,与前人之“信古”及时人之“疑古”皆异。时陈寅恪作审查报告云:“窃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是书自30年代以来重印多次,为国人习中国哲学之标准教科书;英文版早在美国印行,而日、韩等国则多径以此书中文版为教科书者。盖此书于历代哲学家思想之论断,多已成为本学科之典范,故此书实为现代中国学术之经典,而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后40年代,先生以思想学术最臻圆熟之时,作《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of Chinese Philosophy),其深入而浅出,举世称之,是为又一经典。
1937年日军大举侵入,清华内迁,与北大、南开合并而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随校南行,吊屈贾于长沙,怀朱张于祝融,折臂于河内,动忍于昆明,颠沛流离十年,乃先后撰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建成中国现代最完整之哲学体系。先生《新原人》序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则民族之兴亡与夫历史之变化,固激发于先生多矣,而其忧国报民之胸怀亦跃然呈露。先生尝为联大撰校歌歌词,中有“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两句,正先生之写照。抗战胜利,先生又撰联大纪念碑文,中云“盖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数语实为先生后来根本信念而终老不变者也。
1930年起,先生长期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清华领导之核心,对清华教务贡献甚大。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辞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次年参加土地改革。是时国人群情振奋,社会气象一新,先生以为当追随人民、追随新社会,故用心研习马克思主义,检讨往昔哲学,以跟随时代。1952年,以院系调整之故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此后数十年,理论界与教育界时常对先生思想提出批评,先生皆怀与时俱进、择善而从之心处之,然亦不放弃答辩与哲学思考的权利,而其往昔哲学思想往往复萌。如1957年先生撰文阐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批评时人对中国古代哲学否定太多,又提出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以解决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此文即引起诸多批评讨论,先生皆一一慎思明辨而申答之。50年代以后,先生专理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业,每年皆有多篇论文发表,而于孔子、老、庄著力尤多。至1960年,始得允许独立撰写中国哲学史。按旧著《中国哲学史》先生在40年代即冯友兰先生欲重写,而未得其缘,至是,乃以《中国哲学史新编》为题,复参考黑格尔、马克思,重新撰写之。方始出版两册,“文化革命”骤起,以故耽迟达十余年。
60年代后期,先生已年逾古稀,却遭批判、抄家、劳动乃至隔离之厄,痛苦难堪,后以最高指示得以稍缓。时书籍悉被封存,报纸有口号而无消息,激进思潮裹挟一切,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尤可叹者,领袖崇拜靡盖社会,世人鲜不醉于其中,影响所及,先生亦不能免,故曾随顺大众,参加批孔运动。外间对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势皆需身置此特殊时代特殊环境始可了解,岂可以常情而臆议之。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迷思破除,自信复立。先生精神焕发,当耄耋之年,以旧邦新命为怀,继续《中国哲学史新编》之作。先生此时,信心而著,无所依傍,其中多“非常可怪之说”,往往不同于时论。先生以“修辞立其诚”自勉,谓“若因此不能刊印,吾其为王船山矣”。其书全7册,凡81章。先生晚年多病,尝言“《新编》未完,故需治病,若书写成,病即不需治矣”,书成不数月,先生安然辞世。
先生学术贡献,为举世所公认,先后得授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47)、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1)、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82)。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院士评议会委员,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其他学术荣誉,不胜枚举。先生于学术之外,对教育行政亦多属意,早在中州大学时即有心试于校务,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达18年,教绩卓著;抗战中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对三校合作,亦殊多贡献。先生在清华又曾几度代理校务,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其维持爱护教育之功,实不可没。先生尝自叙其学“三史论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者,《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即“贞元六书”。故三史六书为先生学术之代表作。先生中西文著作共30余种,各类文章逾500篇。遗书集为《三松堂全集》,共14卷,超600万言,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晚年居北大燕南园,其院内有松三株,因名室焉。先生妻任氏,讳载坤,字叔明,扶持相与60年,先先生13年卒。有女名钟璞,笔名宗璞,名作家,先生晚年起居多赖之。先生尝谓其平生得力于三女子,即母吴氏,与任氏、宗璞也。
先生实为吾国之硕儒,现代之大哲学家。自幼颖悟过人,性至孝,能诗文。长而好理学,诣理既精,究于物象之表。其为文不事雕琢,平易明白;与人言缓而有条,不乏风趣;授课喜引笑话,颇见幽默。其平居也,无一日不读书写作,无一日不闻问时事,规律甚严而自奉甚简。其于后学也,有问必答,平等待之,未始有厌容。平生最喜《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以为中国哲学之精神,晚年亦笔书成联,挂于东墙,谓之先生东铭可也。先生学问特重精神境界,于宋明道学受用甚深,其心气和平,从容自得,精思志道,惟“有道气象”可以称之。晚年病目,尤喜静坐默诵,而其和乐气象则未尝一日而变。疾革时,遗言嘱门人,谓“中国哲学必大放光彩”。既卒,《纽约时报》竟以长文悼念之,足见先生之影响实已遍及世界。
人不可以苟富贵?
今天正好是北宋大文豪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逝世919周年。苏轼在20岁那一年写了一封书信,后人为了拜读方便,给这封信起名为《上梅直讲书》,信中有一句名言曰: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大意为:人既不能苟且于眼前的富贵生活,但也不应该无所作为而过着贫贱的生活。
苏轼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主要是向当年的考官表达知遇之恩,同时还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以及对考官的敬仰之情。
如果了解完这份书信产生的历史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这句话。
古代文人实现人生抱负的最好方式,无非就是寒窗苦读,再参加“科举考试”,若考中就可以进入仕途,发挥自己的才干。
科举考试按照级别由低到高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除过童试一年一考之外,乡试、会试、殿试都是三年才能考一次。殿试由于级别最高,往往被安排在宫殿里进行,由朝中大臣,甚至皇帝本人来监考。
苏轼同样是沿着这条轨迹实现个人抱负的。
1057年,苏轼20岁,他的弟弟苏辙18岁,都处在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兄弟二人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一块来到京城开封参加殿试,主考官是文坛泰斗欧阳修(1007年——1072年),时任翰林学士,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参评官是著名诗人梅尧臣(1002年——1060年),时任国子监直讲,属于五品官衔。监考的两人不但权高位重,并且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作为学生辈,苏轼对他们非常崇拜。
在考试中,苏轼发挥出色,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了他对时事的看法。梅尧臣读完文章后眼前一亮,大为赞赏,立刻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完觉得也很不错,认为苏轼小小年纪就能写出如此透彻、深刻的文章,并且思想还不流俗,将来肯定大有作为。于是,两人商量后,秉持爱才惜才的态度,决定录用苏轼。
考试结果出来后,苏轼高中榜眼。得知消息后,苏轼心花怒放,怀着崇高热情写了那份《上梅直讲书》。当年的状元是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章衡(1025年——1099年),后来成为苏轼的好友,其他被录用之后又成为栋梁之才的人还有曾巩、苏辙、章惇等。
要深入理解“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这句话,就得结合苏轼的人格理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
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父亲苏洵非常有才华,在诗文上颇有成就。苏轼和苏辙出生后,苏洵把他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两个儿子,并激励他们要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读书,将来要超过自己。
自小,苏洵教导两个儿子,督促他们熟读《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尚书》、《左传》、《史记》等经典著作,以及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大诗人的诗作。
在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和诗作中,一个个古圣先贤的高风亮节和思想格局让苏轼大开眼界,思想迅速得到升华。由此,在以后的道德修养上,苏轼都以这些“士大夫”作为榜样,尤其对大儒孟子的学问、文采、人格,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后来的多篇文章里谈到他。并且,苏轼常常把孟子的一些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在社会背景上,北宋王朝实行“文人治国”,这种弊端在后来一步步体现出来。到宋英宗时期,朝廷内忧外患的情况日益凸显,朝廷内部腐败,外部经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和掠夺,面对内忧外患,朝廷无力改变这些。
苏轼作为有担当的文人士大夫,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度体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理想。因此,他决定认真读书,尽早进入仕途,为国家鞠躬尽瘁。
可以看出,苏轼所说的“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这句话,跟《孟子·滕文公下》里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还融合了孟子《尽心章句上》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意思。
孟子前句话是在表达士大夫面对人生诱惑和人生逆境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人格理想,做一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后句话则表达了士大夫在不同的人生处境时,要有不同的做人原则,把士大夫精神发挥到最大化。
苏轼这句话包含了孟子这两句话的精髓,却又着重表达了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倡导人们做人要正直厚道。
因为在苏轼生活的时代,许多富豪、地主依靠隐瞒土地数量的方式,来损公肥私,导致朝廷的财政收入连年锐减,财政赤字现象非常突出,向来国富民强的北宋王朝在此时竟然出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
这一切苏轼看得明明白白,所以,他在信中就写出了那句话。
在苏轼看来,人追求财富并没有错,但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用正当方式去获取财富。一个人如果已经拥有财富,就不能自私冷漠,只顾享受奢侈生活而不管他人,要肩负起社会担当,怀有一颗济世的善心。
但是,人也不能胸无大志,不去追求财富,向贫穷认输,因为“一分钱也会难倒英雄汉”,过度的贫穷会造成生存危机。连自己都安顿不好的人,又怎么能帮扶他人?
从苏轼在20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格局来看,他是真正的文人士大夫,欧阳修和梅尧臣对他并没有看走眼。在后来,苏轼还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真正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精神。
为什么很多人说他不是真正的热爱足球?
楼主搞这个问答出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他不是真的想问这个问题?
头条搞出这个悟空问答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他不是真的想问到或看到什么问题与答案?
我来告诉你真相。只有两个字——流量!
楼主为了流量,节操都不要了,就为了蹭热点。有了流量,就有钱。
所以,很多人节操都不要了,道德也抛弃了,社会公认价值观也违背了。为了啥,为了流量,为了博眼球,为了哗众取宠。
这些,就是败类,是渣滓,是蛀虫。那为什么还有人关注?因为推送啊
呵呵哒,这就是精准算法,骗流量。
学哲学有什么用?
哲学有什么用?是啊,当代经济社会,哲学有什么作用呢?找工作的话,很有可能就失业了,有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什么为社会、为世界创造什么价值了?而我说,哲学,是无用之大用!理由如下:
1.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哲学是总结各门科学的经验,却又独立于其他科学的一门独立科学。曾经有人说过,当科学家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攀登上科学的顶峰的时候,哲学家们已经在那儿喝茶了。
2.哲学,是思维之思维。哲学,是对思维的再思考。当我们产生一个想法的时候,哲学问题就是会对我们这个想法进行思考。这个再思考的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并不是回到起点。这样的过程,能够产生思想的革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综述一下,这个世界,终究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统治着——或许我们不知不觉,但是我们的任何行为,都被一种思想统治着。为什么总说西方和我们东方有很大区别,根本原因就是东西方的思维极其思维方式不太一样。哲学,就是无用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