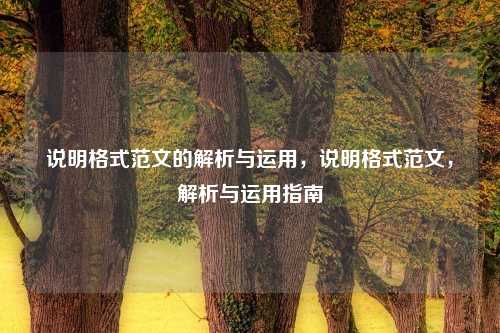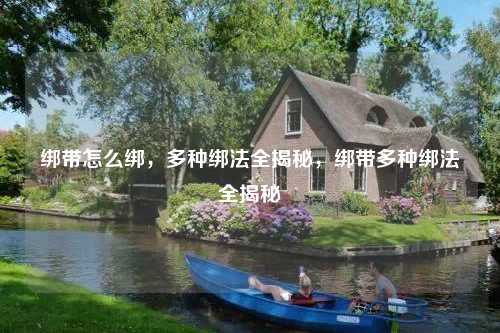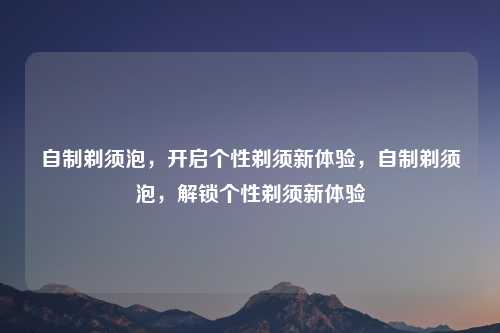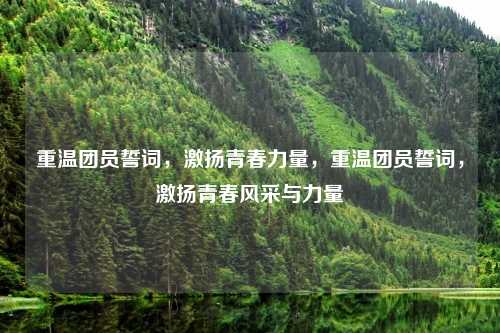峤怎么读,司马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峤怎么读,司马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懿有两个儿子,老大为司马师,老二是司马昭。 司马懿未死之时,司马师已有很大权利,在弟弟司马昭之上,吴国蜀国就是被他们兄弟灭的、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魏国军权,很是嚣张,古语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意思就是司马昭想做皇帝,后来司马昭死后,儿子司马炎被迫魏元帝禅让给自己。
晋武帝本人是继承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的基业而称帝的,但本身并非英明之君,罢废州郡武装、大肆分封宗室、允许诸王自选长吏和按等置军与无法处理少数民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的原因。

统一三国以后,司马炎一下子变了,原来很节俭的他追求起了奢靡的生活,没有了对立的政权,他开始丧失了进取心。除了大兴土木、大修宫殿外,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是在后宫的驾羊车游幸。
在统一吴国的时候,司马炎将原来孙皓的后宫美女五千多人全部弄进了自己的后宫,使总人数猛增到了万人以上。美女多得让司马炎无所适从,只好想了个办法,用羊拉着辆车,自己坐在车上,任凭羊拉着他在宫中自由地漫游,羊最后喜欢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前,他这晚上便住在谁那儿。那些一心想讨皇上欢心的宫女们便想出了办法,把竹叶插在门前,然后把盐水洒在门前的地上,以此来诱惑拉着皇帝的羊儿在自己门前停下来。
总体来说,我认为司马炎前期圣明,后期昏庸,因为统一全国后竟然放弃全国武装,最终导致西晋皇权争夺中,中央无兵可用,外戚专权,匈奴入侵!
窃秦之爵原文?
作品原文1、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2、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3、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4、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5、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6、颍川太守髡陈仲弓。客有问元方:“府君如何?”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如何?”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伛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惭而退。
7、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8、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
9、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曲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10、刘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
11、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12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13、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
14、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15、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
16、司马景王东争,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17、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18、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19、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20、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21、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22、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23、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24、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嵬以嵯峨,其水押渫而扬波,其人垒砢而英多。”
25、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颍,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26、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27、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耳。”
28、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
29、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30、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31、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32、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33、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觉,谓顾曰:“此子珪璋特达,机警有锋。”
34、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
35、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
36、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37、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逆谋,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王丞相诣阙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38、郗太尉拜司空,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
39、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40、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41、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继承司马家族事业的不是司马攸而是司马炎?
为什么司马昭死后继承司马家族事业的不是司马攸而是司马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司马攸到底是什么人。
司马攸,晋文帝司马昭嫡出次子,晋武帝司马炎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按理说,司马炎是嫡长子、司马攸是嫡次子,依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司马炎作为司马昭的继承人没有任何疑问。问题在于一次过继程序,因为司马昭的胞兄司马师一生虽然生了娃五个孩子,却都是女儿。在那个只有男丁才有继承权的时代,司马师只得从胞弟司马昭的儿子中过继一个作为嗣子,司马师过继的这个嗣子就是司马攸。在中国古代宗法层面,过继嗣子等同亲子。换言之,从过继给大爷司马师开始,司马攸理论上已经不再是司马昭的儿子,而是他大爷司马师的儿子!
如果是一般情况下,这种过继并不会造成下一辈的继承问题,因为理论上司马攸已经不再是司马昭的儿子,他无权继承司马昭的晋王之位。可问题又来了,司马昭本身就不是司马懿的嫡长子,他的胞兄司马师才是司马懿的嫡长子兼继承人。司马昭是以“兄终弟及”形式接的司马师的班,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通俗讲就是原本应该是司马攸继承的江山被他亲爹司马昭给继承了。如此一来,司马昭把江山传给谁就比较纠结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江山理应是嫡长子司马炎的,可司马昭的江山本就应该是司马攸的,不是吗?到底让谁接班?司马昭纠结了……那么,司马昭为何最终决定将晋王之位传给司马炎呢?
形势需要司马昭去世时,司马氏虽然彻底架空了曹魏皇帝,但是还没有正式改朝换代,司马昭面临着曹操同样的形势——江山来路不正。接下来由儿子改朝换代是必然,对于晚年的司马昭而言,稳是第一位的,只有政局稳定才能保证政权平稳过渡。可一旦立司马攸为储,司马炎与司马攸兄弟阋墙很难避免,加之司马炎背后的杨氏家族推波助澜,司马氏很可能就此陷入内乱,这显然不是司马昭愿意看到的。
大宗转移已成事实虽然司马攸名义上属于嫡长房,是原大宗之后。可问题是,在司马昭“兄终弟及”之后,司马氏的大宗已经由嫡长房转移到了嫡次房,彼时的司马昭才是大宗,作为大宗嫡长子的司马炎是名正言顺的大宗合法继承人。
彼时的司马氏已经完全架空了曹魏皇帝,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司马昭而言,给后世确立一个皇位传承的标杆才是当务之急。一旦将晋王之位传给原大宗之后,等于是给了后世埋下了内乱的祸根。不仅司马炎与司马攸之间会祸起萧墙,司马氏后世的帝王们也可能会有样学样,一旦遇到类似情况,内乱几乎是必然!与其如此,倒不如将这种内乱的可能性扼杀于萌芽之中,皇位必须由大宗之后继承,管你原来是不是大宗,只要大宗转移了,就只能按新的大宗来论!毕竟大宗转移这种事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常见的,司马昭不得不提前考虑所有可能得负面影响。
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虽然有前面提到的两点,但司马昭依然是纠结的,毕竟司马攸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时候,平衡合派政治势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司马攸的岳父贾充作为弑杀曹髦的策划者深得司马昭的信任,势力也越来越大。如果再让司马攸成为继承人,贾氏外戚势力继续做大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司马昭虽然信任、重用贾充,但作为“帝王”,对臣下的一切信任都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坐视贾氏家族做大。
与此同时,对贾充有成见或存在利益冲突的朝臣几乎都倒向了司马炎。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立司马攸为储,朝臣两派势力争斗几乎无法避免。为了避免贾氏家族做大、也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群臣派系斗争出现,适当压制贾氏家族势力是必要的。立司马炎为储,既可以避免贾氏家族做大,又可以利用司马炎背后的杨氏家族制衡贾氏家族,形成新的权力平衡,一举两得,司马氏可以永远居于不败之地。
只可惜,司马昭算得到眼前,却看不到未来,最终司马氏还是毁在了贾氏家族手中……但贾南风弄权是后来的事了,司马昭毕竟不是神,他只能看到眼前,哪里看得到孙子辈的事情。
司马昭的私心除了政治原因,司马昭的私心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司马攸虽然是司马昭的亲生儿子,但他已经被过继给了大爷司马师,理论上他是司马师的儿子。如果司马攸继承了晋王之位,将来改朝换代成了皇帝,司马师才是“皇帝他爹”,司马昭这个“叔叔”到底该如何定位?追尊“父亲”司马师为皇帝理所当然,但追尊司马昭这位“叔叔”为皇帝,总归有那么点儿名不正言不顺,不是吗?
即便司马攸追尊司马昭为皇帝了,太祖的庙号司马昭肯定是捞不着的。到头来,很可能司马师后来的世宗就是司马昭的了,而司马昭的庙号太祖恐怕就只能是司马师的了……很显然,司马昭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自己忙活一大通,结果让胞兄司马师成了太祖,自己却成了“宗”……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现实权力平衡、给后世树立标杆,亦或是维持政局平稳等诸多方面而言,司马昭传位给司马炎都是最佳选择。与此同时,如果传位给名义上的“侄儿”司马攸,司马昭本人的历史定位也成了大问题。只有让儿子接班,司马昭才是名正言顺的“晋太祖”,让司马攸接班,太祖只能是司马师,司马昭作为“叔叔”,充其量恐怕也只能是个“宗”了。于公、于私,司马昭都只能选择司马炎而不是司马攸。
qiao二声能和哪些整体认读音节组词语?
汉语拼音qiao 第二声有这些字:乔、桥、侨、荞、峤、硚、翘、谯、鞒、憔丶樵、瞧。能与整体认读音节组成这些词:石桥,shi qiao 都是读第二声,其他字无法和整体认读音节组词。而且几个字不是很常见,所以要组成词语有一定的难度,况且要和规定的整体认读音节组词难度更大。
世说新语德行篇?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箸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箸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不失雍熙之轨焉。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箸青布裤,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巾军)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闲,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
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即日焚裘。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涟。见者以为真孝子。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