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行书是,柳公权的楷书能够称为唐代第一吗
天下第一行书是,柳公权的楷书能够称为唐代第一吗?
很肯定的说,柳公权的楷书不能称为唐代第一,原因很简单,颜真卿的“颜体”与柳公权的“柳体”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美誉。换句话说,颜真卿的楷书就可以与柳公权的楷书相媲美,而且还有欧阳询呢,自然柳公权的楷书无法称为唐代第一,
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又学欧体挺拔劲峭、内紧外松的结构特征,学颜体的点画顿挫强烈、结体圆转外拓,但柳公权融会贯通,形成自家面目,下笔更为劲健。清人刘熙载说他学欧阳询的《化度寺碑》,说他的《玄秘塔碑》出自颜真卿的《郭家庙碑》,这就说明了柳字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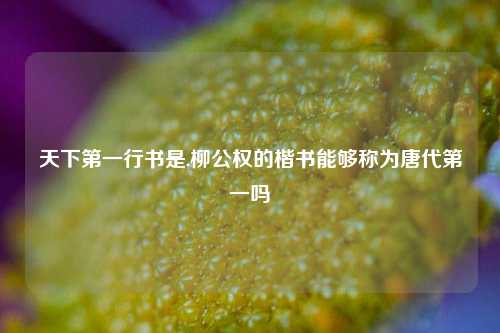
后人学柳体学得最多的便是《玄秘塔碑》,此碑取欧体之方与颜体之圆,可称方圆兼备,点画清劲峻拔,顿挫规整,结构谨严,有疏朗开阔的神情和方整清新的神采。康有为说它如果缩成小楷,则“尤为遒媚绝伦”。综上所述,这些就是柳公权的“柳体”特征以及后人对其书法的崇高评价。
即便如此,柳公权的楷书也无法称为唐代第一,最主要原因是,欧阳询的楷书点画精确、结构谨严,达到了所谓“一画不可移”的境界。欧书还很富于变化,在端庄凝重之中表现出生动的变化,欧书注意主笔,这明显继承了隶书的写法。可以这么认为“欧体”的风格,柳公权的楷书中是绝对没有的,或者是无法媲美的。
冯承素为何称天下第一行书?
冯承素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而不是冯承素写的书法。兰亭序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是东晋文人雅士在兰亭聚会时大家饮酒作诗,记录当时盛况的一篇文章,据说王羲之乘着酒兴而写,待酒醒后重写,再也写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真迹去哪了?
关于《兰亭序》流传失踪的故事,其精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兰亭序》本身。各位看官,故事有些长,耐心听豆子慢慢道来。
流传有序话说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约了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会稽山兰亭溪畔,搞了一场盛大的野餐趴。来的都是文化人,助酒兴自然不能靠猜拳,必须要吟诗作赋才应景。其中26人,当场作诗41首,汇编成册,是为《兰亭集》。王羲之非常高兴,觉得你们这些人太给面子了,我来写个序言吧。于是在酒酣耳热之际,写下了著名的三大行书之首——《兰亭序》。
估计是也喝多了的缘故,这《兰亭序》全文28行、324字,写的是遒媚飘逸, 字字精妙, 有如神助,其中有20个“之”字,竟无一雷同。王羲之酒醒后一看,惊呆了,问道:“这是谁写的?怎么写的这么好?”下人们说这就是老爷您写的啊,王羲之楞是不信。后来他多次重写,也确实没能超越最初的版本。
王羲之知道,这《兰亭序》,可能是他一生书法生涯的最高峰了,于是小心保管,不示于人。但是防火防盗,防不住老丈人,《兰亭序》被郗鉴要走了,在他那边传了两代,不知为何又回到王氏后人手中。就此一直传到了王羲之的七氏孙,智永和尚手里。
智永和尚原名王法极,少小出家为僧,也是一个“书痴”。他在云门寺出家时,盖了一座小楼住在里面,声称不练好字绝不下楼,留下了“退笔冢”、“铁门槛”等书坛佳话(感兴趣的看官可以搜索一下,篇幅有限,我就不展开说了)。
智永和尚活了一百多岁,可他没儿子啊。临终时,把《兰亭序》传给了他最喜爱的徒弟,辩才和尚。
辩才和尚也不是普通人,他是梁朝司空袁昂的玄孙。袁昂以忠诚闻名于世,且颇有才名。辩才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为人重诺,一言九鼎。按道理说,智永把《兰亭序》托付给他,颇有识人之明。只可惜,辩才遇到了历史上最牛逼的王羲之“铁粉”:李世民。
李世民的欲望李世民坐稳江山后,原来的马上皇帝不知怎么的雅兴大发,酷爱书法,尤爱王羲之。他在民间大肆搜寻王羲之真迹,一但得之,便爱不释手,珍藏身侧,时时临摹揣度。不仅如此,他还亲自给《晋书》作《王羲之传》,总之,称其为王羲之最大“铁粉”并不为过。
但是李世民一直以来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找到《兰亭序》的真迹。后来,他终于打听到《兰亭序》在辩才和尚手里(估计是虞世南告的密,虞世南身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是李世民的近臣,同时又是智永和尚最看重的俗家弟子)。于是请辩才入长安主持法事,期间言谈话语之中,一直打听《兰亭序》的下落。辩才和尚也不是傻子,坚称没见过。如此反复三次,辩才和尚干脆写了一首《赴太宗召》:
云霄咫尺别松关,禅室空留碧障间。纵使朝廷卿相贵,争如心与白云闲。翻译一下就是:不给不给就不给!
这下李世民没招了,自己怎么着也号称明君,总不能硬抢吧?但是又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呢?房玄龄看李世民为了这《兰亭序》抓心挠肝的,就推荐了一个人,监察御史萧翼。
萧翼的巧取豪夺萧翼是梁元帝的曾孙,饱学之士,机巧多变。房玄龄说,让他去,一定有办法。
萧翼接旨之后,哭笑不得,心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让我去当坏人。但是皇命不可违啊,萧翼对李世民说,让我去也行,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第一,我把《兰亭序》拿来给你,就算完成使命,你别管我是怎么弄到手的。
第二,给我两张王羲之的杂帖当做道具。
李世民欣然应允。这萧翼也确实有办法,把自己打扮成落魄书生的样子,风尘仆仆的去了云门寺。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再加上萧翼乃是皇家后裔,风度自然不同凡人。他在云门寺刚一露面,就引起了辩才和尚的注意。两人先是寒暄,逐渐言谈深入。萧翼事先做足了准备,句句言语皆从辩才的兴趣出发,不两日,两人就引为知己,无话不谈。
过了几天,萧翼看时机成熟,拿出了从李世民处要来的王羲之杂帖,请辩才品评。辩才看过之后,称此虽是王右军真迹,但为凡品。萧翼假意不服,几句言语挤兑,辩才按耐不住,从秘密的暗格中取出了《兰亭序》给萧翼观摩。萧翼这老狐狸装作毫不动心,反称辩才的《兰亭序》是假的,两人争论半响,没个结果,就约定明天再辩。
如此反复两天,辩才就对在萧翼面前出示《兰亭序》毫无戒心了,也不曾再将其放回暗格,以便萧翼来时,随时评辩。
一日,辩才出门赴家斋(其实也是萧翼安排,调虎离山)。萧翼来到辩才住处,对看门的小和尚称有手帕忘在屋里。小和尚这几日与萧翼早已熟悉,痛快开门。萧翼卷起放在书桌上的《兰亭序》就跑,一路快马加鞭,窜到了永安驿站。
在永安驿站,萧翼招来越州都督齐善行,表明自己的御史身份,请齐善行传辩才来见。辩才的饭局还没结束呢,莫名其妙的赶来驿站,一看萧翼竟是李世民的监察御史,还拿出圣旨,装模作样的称赞辩才献出《兰亭序》,一通感谢。顿时怒急攻心,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这边厢李世民终于得了梦寐以求的《兰亭序》,欣喜若狂,提萧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赏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宫内御马两匹、 配珠宝鞍辔,宅院、庄园各一座。
过了几日,李世民良心发现,觉得辩才和尚年事已高,自己这样骗一个老人家,似乎有些不要脸。于是赏辨才锦帛三千段,谷三千石,命越州都督支付。(估计齐善行一定气的跳脚骂娘:“本来我就是个跑龙套的,不给盒饭也就算了,最后结账又想起我了?”)
可怜辩才和尚,得了赏赐也不敢用,兑换成了钱财,为云门寺盖了三座宝塔。现在看官们去到绍兴云门寺,仍然能看到“辨才塔”的遗址。辩才和尚受了此番惊吓,同时自觉愧对智永恩师,一年后郁郁而终。
失踪之谜李世民得了《兰亭序》后,好好显摆嘚瑟了一番,命宫内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各拓数本, 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近臣。此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的临本传世。我们现在各大博物馆的唐代临本《兰亭序》,基本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后来,李世民死了。按照他的遗诏,《兰亭序》是要放在枕头下面的。也就是说,《兰亭序》的真迹,应该作为李世民的陪藏品,埋在昭陵之中。
到了五代之时,十八座唐代皇陵,被陕西关中北部节度使温韬挖了十七座,其中就包括李世民的昭陵。史书上记载,温韬入昭陵地宫后,见其建筑设施之宏丽,与长安皇城一般无二。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床边放着一个石函, 内藏铁匣,铁匣内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书册字画,其中就包含王羲之的数幅真迹。二百年来,纸张墨迹如新。这些珍藏全被温韬取出,千年来不知去向。
但是在温韬的盗墓珍宝清单上,并没有《兰亭序》,而且此后也从未有过《兰亭序》出世的消息。所以有的专家认为,温韬盗墓匆忙,《兰亭序》应该还在昭陵的某个角落里,并未流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李世民的遗诏中,并没有明文要求《兰亭序》陪葬。所以有可能将《兰亭序》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同样喜爱书法艺术的唐高宗李治。而李治在死之前,曾明确传旨,要求将自己喜爱的字画随葬。所以《兰亭序》可能不在昭陵,而在李治的乾陵之中。
有趣的是,盗墓贼温韬唯一没盗的唐代皇陵,就是李治的乾陵。史书记载,温韬挖到乾陵之时,风雨大作,遂无功而返。这似乎又增加了《兰亭序》埋在乾陵的可能性。
总之,千古第一行书《兰亭序》,随着李世民父子的死亡,从此渺无音讯,成为文化史上令人遗憾,却又极为迷人的著名悬案。也许,等我们有能力发掘昭、乾二陵时,才能得到《兰亭序》在哪儿的最终答案。
再多说一句,如果昭、乾二陵里面都没有,那……就真的要成为解不开的谜团了。
颜真卿祭侄文稿为何不是天下第一行书?
中国人对座次很感兴趣,《隋唐演义》里给众位大咖排出个“第N条好汉”,《水浒传》中“英雄排座次”也是很热闹的一章。国人对“第一”“首次”“首创”等尤其感兴趣。
这也难怪,这好比版权,我占据了第一的位置,其他人得交“版权费”,这是知识产权。哈哈。
关于《兰亭序》和《祭侄文移》,哪个艺术性更强,历来是有争论的。
《兰亭序》能名列“行书榜”首席,除了《兰亭序》的字确实写的很美,除了《兰亭序》的文章确实写的很美,除了“兰亭雅集”确实是一次文坛盛会,除了唐太宗的极力推崇,更重要的是,王羲之在书坛的江湖地位,说他父子二人合力创建了今体行书的书法体系,一点也不为过。
任何事物占据了时间先后上的优势,就占据了先发优势。在书法上,虽然有人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过于媚俗,但这只是艺术观点的不同,毕竟后代行书几乎都源于二王行书,这一点是历史无法改变的。
作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其艺术水平是勿庸置疑的,虽有赵佶说颜字笔画粗陋如“田舍汉”,也有米芾的“颜柳挑踢”之说,但这些异议指的是其楷书,至于行书,尤其是其代表作《祭侄文稿》,则几乎没有其他说法。
但颜真卿输在晚生几百年上,在他学书初期,不可避免地从二王入手,从二王中吸取营养,再参以篆隶笔法及民间书法笔意,终于创造出独特的颜体行书,并与王羲之并列为书坛的两座高峰。
中国有句古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将功成万骨枯,历史只会记住卫青、霍去病、郭子仪、岳飞,至于无数的兵卒,只能成为“炮灰”。
而文学、艺术,因每个人审美观点不同,纯以艺术来考究,怕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其对历史的贡献,以及其出生的早晚,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行书榜”的排名由来以久,我们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个顺序。
更多文章,敬请关注千年兰亭。
米芾的研山铭为何被有些人称为天下第一难书?
因为什么?因为提出的人对书法的认知不足呗!
我没有必要去搜寻是谁提出的《研山铭》是天下第一难书,我也不管是那个书法界的大人物,我就是质疑提出的人对书法认知不够高深。
为什么没有人说米芾是书圣?因为米芾真的不够资格!需要说明的是,我对米芾是极其尊敬的,而且在我的心目中也把米芾抬到书法史很高很高的位置。可是,作为书法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这样你能够有机会得到真知,你才能进步。
书法人都知道米芾是王羲之的学生,他也字魏晋书法为毕生的追求。那么,米芾达到了吗?显然没有!终其一生米芾也没达到魏晋的高度,因为什么?一是没能理解到魏晋的书法最高层次,二是难度上达不到魏晋的高度。
所以说,把《研山铭》成为天下第一难书是谬误,是书法认知不够高深的认知!即便可能是苏轼提出的,可是,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是偏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