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同居 冷血大兵,军舰导弹打完了怎么办
暧昧同居 冷血大兵,军舰导弹打完了怎么办?
海战中舰载武器射击的速度远大于补给的速度,而且军舰的弹药补给对于舰艇的平衡要求很高,毕竟弹药尤其是大型弹药在补给过程中因为磕碰等发生爆炸危险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军舰在航行过程中是不能通过补给舰进行大型弹药补给的。名义上的综合补给舰,可以补充的部分包括弹药,但是并不包括大型防空,反舰导弹或者鱼雷这些大家伙,充其量可以在航行中为军舰补给一些子弹或者小口径炮弹,理论上小型防空导弹比如海红旗10那样的小型弹药!这些弹药的重量较小,可以人工装填,所以舰艇在海上导弹一旦打完,应该立即脱离编队后撤,回港进行弹药补给!
综合补给舰对于弹药的补给非常有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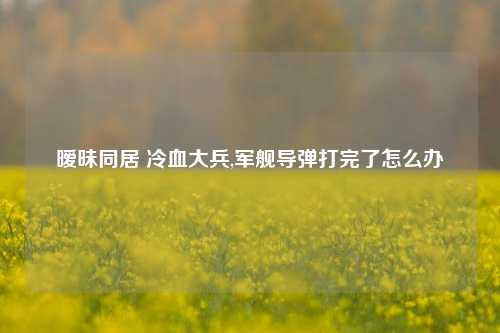
首先说明,其实军舰在海况很好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海上弹药补给的,但是对海况的要求非常高,一个不好因为军舰的摇摆造成弹药爆炸是非常危险的。不过这种补给方式一般不会出现,首先,海况要求高,其次是一艘军舰停下来补给弹药意味着整个编队都需要停下来,而在瞬息万变的海战战场上,不可能为了一艘战舰补给而将整个舰队停下来!
航母可以采用垂直补给的方式进行补给关键是现代垂发装置的不及速度非常慢,一半连同发射筒在内的弹药一起更换,一个发射筒的吊装时间需要20分钟,完成一艘几十枚发射筒吊装的驱逐舰的弹药补给时间高得惊人,像美国宙斯盾驱逐舰那样,需要差不多30个小时才能完成一艘阿利伯克级的弹药补给,一昼夜还要多的事件站在那里补给,还打不打仗了?所以大部分军舰的弹药都是在港口补给,海上补给只是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中不会在海上进行补给!
我国军舰的补给因为发射方式的不同,补给方式也是千奇百怪,一般倾斜发射的弹药的补给相对简单,可以直接连同发射筒吊装上去固定好就完了,甚至可以一次性吊装两枚导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倾斜发射的补给都是这么容易。咱们从俄罗斯进口的现代级驱逐舰发射的日炙导弹的发射筒是固定死的,不能取下来,要对其进行补给,只能从发射口用导轨将导弹滑进去,这和潜艇通过鱼雷发射管补给鱼雷非常类似,这种补给是最慢的,对于精度要求也非常高。
大型弹药一般是吊装补给的,但是不是在海上,而是在港口内大家对于我国防空驱逐舰的补给应该比较感兴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我们的盾舰是如何补给垂发弹药的。首先是052C,这是延续俄罗斯的设计,通过打开左轮式发射桶的舱盖,内部有肘节装置可以将导弹竖起来,这需要舰上的起重机将导弹二次传递,将港口吊装上舰的海红旗9再一次吊装在肘节装置上竖起并送入导弹发射桶,相对于052D直接从岸上吊装,速度慢了很多!
阿利伯克级舰上起重机的位置022导弹艇直接将导弹舱打开进行吊装补给现代级反舰导弹的补给非常复杂052C的吊臂起重机位置052D和054A是可以直接在岸上将导弹直接连同发射筒竖起来,然后直接将导弹发射筒垂直吊装起来将其装进垂发装置中。这种设计的好处就是可以快速地将导弹装进发射筒,不需要再像052C那样经过二次吊装,速度上快了不少。当然,这并不是说052D没有设计舰上起重机,052D也设计了占用三个垂发装置的伸缩式起重机,但是使用起来效率比较低,所以一般052D的舰上起重机并不怎么使用!052D直接吊装的补给方式054A的补给方式也非常快捷潜艇的装填其实和垂发装置的装填是一样的,只不过潜艇的装填精度要求最高,是目前垂发系统中最难以装填也耗时最长的。除了垂发弹道导弹,潜艇的鱼雷装填是利用在潜艇鱼雷发射筒前方设置一个浮动平台,让鱼雷从发射筒反向顺进去的,这种方式速度也比较慢
我国潜艇正在补给鱼雷军舰弹药尤其是大型弹药的补给,一般都不能依靠人力完成。过去那种主要携带倾斜发射装置的军舰,因为载弹量少,补给空间比较大,所以一般吊装比较容易,速度也非常快。但是现代垂发装置的弹药补给速度非常慢,一个是数量少,另外一个,弹药的补给空间小了很多,舰艇的结构也非常紧凑,一艘军舰在战时可能三两个小时就能将弹药消耗一空,但是补给一艘军舰的弹药,随随便便都是以天为单位进行计算的!
多大烈度的海战才能将舰上弹药消耗一空?我们讨论的是军舰打完弹药之后怎么办?那么您知道多大烈度的战争才能将弹药消耗一空吗?我们假设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战时配置的防空舰数量大概是5艘,每艘军舰配备垂发的防空导弹70发,近程防空海拉姆10枚。也就是说,仅仅防空这一种导弹的携带量,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携带了400枚。
如果假如防空作战每防御一个来袭导弹和飞机,消耗2发防空导弹,那么意味着航母在防御的过程中要防御200个目标才能将导弹全部消耗完。假如这200个目标都是飞机的话,那么需要像日本,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才具备这样的实力。假如这200个目标都是导弹的话,那么需要像中国和俄罗斯才具备一次性发射200枚反舰导弹的实力。说到这里您应该可以想到,基于现有海军实力的作战需要,军舰携带弹药量是足够的,一般不会打空,除非处于大国间大规模战争状态中,否则不会出现如此大烈度的战争!一旦舰队军舰经常回港补充弹药,那么这个世界的状态就可想而知了!就连二战时期不列颠空战那么有名的战役,英国和德国所消耗的飞机数量不过才100多架,要消耗一艘现代化大型军舰的弹药对战争的烈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平时和战时的配置不一样,一般在战时,应对的舰队力量配置就会加强,这回根据任务的难易程度灵活调整舰队的规模。未来海战状态下,大国海军在应对需要一艘航母出动的威胁时,最少会三艘以形成数量优势,在战场上力求形成兵力碾压优势,大部分时候舰载机就把战争打完了,所以也就不存在军舰导弹打完的情况了!
80年代很穷但为什么离婚率很低呢?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80年代的离婚率,也不能说很低。
1987 年中国离婚率为 0.55 ‰,到 2019年的离婚率为离婚率为 3.4‰,差不多是6倍的差距。
表面上,1987 年的离婚率似乎不高。作为一个比较封闭、民风保守的社会,这个比例并不少,日本至今离婚率不过1.77‰。
中国离婚率是从80年代开始,疯狂飙升起来的。
80年代之前,离婚并不容易,一般要组织上批准才可以。
夸张的是,当时并不认为感情破裂就是离婚的唯一标准,甚至都不是标准。
在1980年,中国通过了新的《婚姻法》,离婚条件中明确写了一条,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
以前离婚难到什么地步?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基本就肯定离不掉。如果涉及第三者,哪怕同第三者没有任何不轨行为,出轨者也要倒大霉。
著名的王近山将军,就是《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就因为同原配感情破裂,决定离婚去小姨子,闹得天翻地覆。
最后婚虽然离掉了,王近山却被开除党籍,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调往西华县黄泛区农场改造。
从80年代开始,离婚就比较容易了。基本上夫妻双方同意,就可以离掉,组织上顶多做做工作,并没有拦住不让离婚的权力。
另外说几点:
第一,今天主要是女人离婚。
专家分析,今天由女方主动提出的离婚,占百分之七十四之多。
而八十年代,女方主动提出离婚是比较少的,多是男人要求离婚。
当时社会风气比较保守,人民的观念也保守,尤其对于女人而言,无论认为任何原因离婚,包括被家暴或者男人出轨而离婚,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80年代有个著名的离婚案,就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最初她被反革命的哥哥连累,因几句话就被发配到北大荒农场劳动教养。后文革结束后,遇罗锦因哥哥没有平反,她也无法回城,被迫嫁给一个有些权势的北京干部蔡钟培。
蔡钟培不但将妻子调回城市,有了北京户口,还动用关系争取为遇罗克平反。
等待哥哥平反以后,遇罗锦就彻底恢复了地位,继续担任工程师,时间是1979年。
没想到,1980年遇罗锦就申请离婚,理由是婚姻本来就没有爱情基础,是为了物资利益。
蔡钟培颇为不愤,认为妻子就是利用他以后就甩,拒绝离婚。
有意思的是,法院最终两次判决,到1981年才同意离婚,还将遇罗锦臭骂了一顿:
“遇罗锦与蔡钟培于1977年7月8日恋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当时社会舆论还闹得天翻地覆,连新华社都刊文:《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
为什么新华社也管这种事?
这是因为1978年以后,中国离婚出现很大变化。
以往都是男性提出离婚,女性呼天喊地的闹着不愿意离婚。
但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42.8万对,提高50%。80年代的离婚事件中,女性主动提出诉讼的居多,约占71%,其中知识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多达86.1%。
为什么会这样?大体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风气开始变化。
而中国妇女又同其他国家不同,基本都是有工作,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经济也是独立,有离婚的客观条件。
第二,当年社会风气不鼓励离婚。
上面也说了,80年代离婚案还是相对少的,而敢于提出离婚的基本都是知识女性。
而普通女性哪怕自己有工作,往往也有很多顾虑,不敢离婚。
尤其是乡下妇女,离婚被当作一种羞耻之事,而且还不是妇女一个人丢人,还会连带全家丢人。
所以乡下妇女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婚的。
萨沙记得看过一个案件,还是90年代。一个叫做孙丽的妇女,同一个诊所医生李辉结婚。
婚后李辉回忆妻子作风不正派,怀疑她在外上班会找机会偷人,经常对其进行殴打。
当时报道这么说:今年2月8日,在对孙丽一顿暴打之后,李辉向孙丽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么买断工龄,下岗在家;要么给下体上锁,可以上班。被打得遍体鳞伤、抖成一团的孙丽问李辉:锁上之后还打我不?李辉痛快地回答:不打了。于是,李辉买来了手术用的缝合针、肠线和麻药。当晚,在麻醉剂的作用下,孙丽的下体被李辉缝合上了。之后,李辉竟用一把俗称“将军不下马”的小锁头从孙丽的下体缝针的伤口处穿过,锁住下体。后因孙丽是在忍受不住痛苦,向邻居大姐求救。大姐看到这把铁索以后,极为气愤,直接报警。2月13日,在警方的陪同下,孙丽在一家医院妇科取下了锁住下体的锁头。
看看,当年女人都委曲求全到什么地步了?
如果不是大姐报警,孙丽仍然不会离开李辉。
今天谁敢这样试试看?就算偏远山区的村妇,也会毫不犹豫离婚、报警。
第三,当年离婚后女人会有一系列现实问题。
常见的就是风言风语,认为离婚女人肯定自己有什么毛病。
如果女人漂亮一点,就会被怀疑是狐狸精甚至破鞋。
在80年代如果被扣上一个这种帽子,被人指指点点绝对是轻的,重则当作流氓罪,这是要法办的。
如果女人还有孩子,问题就更严重。
这方面说起来就没边了,不多谈了。
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电影往事
年轻快乐的送水员毛大兵(夏雨饰)在送水的路上撞倒了堆放在路边的砖块,又惨遭一个女孩(关晓彤饰)的暴打。女孩被拘留,却莫名其妙的要求大兵帮忙照看她家的金鱼,当大兵打开 女孩家门的同时。也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小兵和玲玲是在看露天电影中渡过的童年。那个年代,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对电影的迷恋之中。露天电影为老百姓,特别是小兵和玲玲带来无数的梦想和快乐。在玲玲十多岁时,家中发生了一场意外,使玲玲和妈妈(姜宏波饰)之间产生了误会。玲玲离家出走,到处流浪彻底将自己的心灵和生活封闭起来,在歉疚和追悔中蹉跎月。直到那天在另一个城市的街头玲玲与大兵不期而遇,一切才峰回路转。童年的伙伴形同陌路大兵拼尽所有的力量,要帮玲玲寻找回失去的世界 。
对于票房不好的电影一直心里都有抵触,不太喜欢,看完之后这部《电影往事》却打动了我。
姜鸿波扮演的妈妈是我见过的她最美丽的角色。那样的年代里一个未婚生子的女人,挺直了脊梁高昂着头,带大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她那么美丽。她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明星。虽然破灭了却一直怀着对美丽的向往。和女儿在晾满了白色床单的院子里跳舞那一段真的很美。她一直对女儿那么爱护。甚至在别的小朋友和女儿出现矛盾时会很直接很生气很用劲的伸手扒拉那个孩子。她最喜欢周璇。喜欢看她的《马路天使》。在躲住在她家的毛小兵问她什么是天使时满眼憧憬满眼思绪的说:“天使是很善良很美丽的人”。这部影片中的人物都有着天使般的心。玲玲妈妈是一个美丽的天使。她对孩子有着强烈的爱心。不止自己的孩子。对别人也一样。比如脏孩子毛小兵。她并不嫌弃他。对他那么好。 潘爸爸,一直深沉而执着的爱着玲玲的妈妈。在小玲玲说出拒绝认他做父亲的理由是自己的父亲是罗金宝这个影片中的大英雄时,并没有恼怒和嘲笑。而是善良的告诉玲玲她的父亲有着重要的使命所以不能陪她。他让幼小的玲玲继续生活在幸福中。 毛小兵这个脏了吧唧一脸坏笑的小坏蛋!笑起来一脸的傻气。自我介绍时说:“我叫毛小兵,毛主席的红小兵”。脸上在住到玲玲家之前就没有干净过。早早的学会了各种成年人才会使用的生存手段。让人又爱又气。可是他还是一个善良的孩子的。兵兵这个早早离开的小天使!那么那么懂事!那么那么善良!玲玲妈不同意玲玲也去考少年宫,兵兵却为她求着情。在玲玲因为妒恨和愤怒把他偏到其他地方偷偷离开父亲又把他找回来后对妈妈说是自己出去玩走丢了。想着他回来时小脸脏兮兮,小小的身体瑟缩在潘爸爸的怀里的样子,忍不住眼泪掉下来。 玲玲虽然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可是也一样是一个善良的人。虽然毛小兵又脏又学习不好,可是看到他被自己的父亲打的抱头鼠窜时却又把他带回自己家让妈妈收留他。 他们都有着天使般的心。
另外就是夏雨一出来那口说不清楚是哪里方言的独白。呵呵~~真的挺傻挺逗的。 还有就是很喜欢影片的叙事方式。 用玲玲的笔记来做旁白。很喜欢。
总之是一部难得的国内好片。
萧红在文学上是不是被过誉了?
【传媒学术类话题】
谢邀。我写过一篇《巧遇葛浩文》,葛浩文是何方人士呢?是写萧红评传的美国人。本国人夸本国人,故乡人赞故乡人,总不像外国人夸赞得那般有距离美。至于过誉不过誉真该看一看评传。可以说,葛浩文因研究萧红而驰名,被誉为是一个为萧红续命的人。
2009年9月4日,北京,一大早就阴雨连绵,下了一个上午还多。我开车经二环至单位,舶好车后,到对门小饭馆早餐,半屉小笼包,一碗豆腐脑;待工作会议罢,打手机联络儿子,接他一起去国际会展中心,看那里正在举行的以西班牙为主宾国的国际书展。
票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吴英杰送的;两天前我开车送她去昌平王庄看望导演张子扬。我的许多文友,都是多年以前,我在哈尔滨生活、学习、工作期间结识的;在四分之一世纪,可亲可敬的文友,让我印证了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不简单也不复杂的惯性共识。
正是那个时期,我在文字方面,有大约五类事,可算作比较成形系统一些,且现今可建立我在写作经验上的某一族艺术档案:
为多届哈尔滨之冬冰雪节做外宣诗画集及为冰灯游园会景区命名;
为多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写评论和专访乃至扩展到《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
写多届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人民政府市长专访,以庆祝哈尔滨解放与开放;
写多届中共哈尔滨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专访,并拍成电视专题纪录片;
接办《〈哈尔滨日报〉副刊·〈我和哈尔滨〉专栏》数年⋯⋯
恰是末项选题,使我最早知道,美国有位学者专门研究——现在每一个哈尔滨人都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女儿,受到鲁迅首肯的萧红;当年的萧红研究,也就是上个世纪末叶后二十几年,外籍人比哈尔滨的学人们,更为具有个人自信力和国际影响力。这固然,也有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之缘故。
葛浩文致辞此公是葛浩文。我竟在这个国际书展上巧遇葛浩文用英语讲座、汉语答问。关于萧红,我没有向葛浩文提问;葛氏著《萧红评传》,葛氏译《呼兰河传》,都产生大影响⋯⋯这些根本无须再问。
请重温,葛浩文著《萧红评传》序言披露:“有好几个月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写到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愈来愈真实,我写到她从一家医院转到香港临时红十字会医院,我只需写下最后一行,便可加上简短的附录和我的结论。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
要知道,1980年哈尔滨市呼兰县萧红故乡,对葛浩文而言,是怎样的神秘、向往、亲切、热中;他在哈尔滨,参观萧红读过的第一女子中学、萧红笔下的道里商市街等;只要是与萧红有关的地方和人物,他都去,都拜访,例如,谒呼兰萧红故居,与萧军联系晤面。
萧军木刻像/冯羽作正是1980年,萧军携女萧耘、子萧燕,也来哈尔滨小住,是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我听了萧军演讲,也一起照过相,还得到赠书(《萧军近作》《羊》《吴越春秋史话》)和题词(“不蔓不枝”)。我想,我的这些待遇,葛氏一定享有。我写了《萧军赠书》一文,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还写了《华夏才女》一词,敬献萧红灵前。
1986年,我任《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记者,驻哈尔滨友谊宫,与端木蕻良同一幢楼,叩门拜见;他那天刚去呼兰萧红故居回来,为之题词:黑龙江之光。端木蕻良辞世,我写文章追思,发表在《太阳岛周刊》上,回忆了这次见面与谈话。
而我上网才知道,葛氏为萧军、端木蕻良一位位与萧红生活过的人,又是他拜访过的人,陆续地离开人世,竟和自己的亲人离别一样地哀伤不已,是他大动了感情所致!
在国际书展,巧遇葛浩文,我不仅没有向他提问题,也没有请求合影;我当新闻记者多年,采写社会名流众多,现已失去见人就合影的兴趣。对于葛氏更是如此,他从“四十不惑”已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距”之年,毫无可能再图虚名。
我所关注的,是葛氏对汉语言文学的认知深度和当下态度。他说,汉语小说家信笔写作,纯属个性使然,但是,对于英语社会的读者,翻译人的作用在于真正让读者看明白。例如,“除夕”“红白事”“解放以后”,直译就不行,人家看不懂,加注解方可。他讲道,翻译至少要精通两种以上语言;很难想像林纡只懂汉语、不懂英文,却能翻译出《黑奴吁天录》;为此,他说,我不再读任何英译汉的书,而作为翻译只进行汉译英,因为我懂这两种语言。
他举例,原作者、翻译人、出版商,均靠“信达雅”维系,他作为翻译,尊重原作者,不轻易删节,有时候跟出版商交涉,不得不让步;出版商只考虑英语社会读者接受能力阅览习惯,不会照顾原作者感受,对此,他爱莫能助。他译毕飞宇,《青衣》,一句:恋人之间,女叫男哥,这称谓表明有血缘而非恋人;一句:做爱的男对女说,我把你当作女儿。只这一句,已涉及到常纲伦理,言辞令人作呕,必须删改才行。
萧军晚年注释与萧红书他回答,译贾平凹,《浮躁》,根本没删,可以去看,说删是误解;译阿来,《格萨尔王》,发现问题,请其解释,有说明白的,有说不清楚的,他解释得太多,我无法准确地译成一句话,但我西藏的功课做得不深;译姜戎,《狼图腾》,说明2万字,脱离小说本体,只能删去。他重申,我不带研究生,就不会有,由我带的研究生翻译、而我来署名这事发生。人家偏要这么讲,你有办法阻止吗?翻译家费力不讨好,很像鲨鱼在水中游,一旦停下来就等于死去,我不会停下来。最近应约重译老舍,《骆驼祥子》,之前尚有三个译本,没一个理想的。
听葛浩文用英语讲座、汉语答问时,我临近告别,忽地感觉一种冷清;据看车人讲,比较其他展,书展最冷清。这话我信。就在这冷清中,我看到法国摊位的设计与样书绝非一般,中国大陆书展摊位与样书却无一例绝不一般。
上星期五,我看中国美术馆国庆60周年画展,品味欣赏到程丛林原作《1968年 月 日·雪》,好一大幅震撼人心的油画,抵得上十部同题材电视连续剧;还记得,我在西藏拉萨至林芝的途中,那藏胞的民族装束和所居的木质房舍,竟与中国画线描勾勒三国时期人物形象以及天然背景别无二致。于是我坚信,在中国画坛,无论是西洋画法、还是中国画法,畅达的思维开拓,深邃的艺术穿透,一切事物从发生到发展以至于消逝,均逃不出大规律。
国际化、市场化、企业化、商品化,对于书展的设计理念与样书展示,只是形式和手段而已;葛浩文所讲的,给我关键的启示在于,原作者、翻译人、出版商,坚持“信达雅”始终,更存在越位求索、换位思考、对位运作等机缘。图书出版多数时间属于静下来的工作,哪能闹一阵子过去;图书发行呢,商人亦诗人亦哲人,大手笔即大思维即大规律。
一个自大的民族,当然没有大出息;但有的时候,过于自卑也必将误事。记得,早在1993年,我和张子扬等人参与首漂黑龙江之后,他任总导演、我任总撰稿,为中央电视台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搞了一场名曰《冰雪火》的大型电视晚会。就在其中,有段相声,由一法国留学生夸哈尔滨而一中国曲艺演员赞巴黎,我作题为《我说你的 你说我的》。
反串、对比,风趣、诙谐。事后请当地专家评论时却遭攻击,举例,“法:‘我们哈尔滨有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咱们巴黎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这样对比很不恰当,萧红和雨果不能比!”怎么不能比?正是这晚会被澳大利亚公民盗版,由澳警方破案、检方起诉、法院审理,央视请我举证,拿出创作依据,我方最终胜诉。
许久没得闲回哈尔滨看看了,在国际书展巧遇葛浩文引出这许多话来。得到的欣慰是,从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到省内新闻出版界和文学艺术界,最近推出再版《萧红全集》、命名萧红文学院、设立萧红文学奖等举措,坚持传承萧红“黑龙江之光”永久特质品格。
夏志清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经葛浩文之手,萧红、白先勇、王朔、莫言⋯⋯甚至“80后”的春树等二十多位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家的四十多部名作在英语世界呱呱坠地。
我倒怜悯起葛浩文这“接生婆”来,他似乎已握起现代汉语言文学家赢得诺贝尔奖的译笔,不仅“首席”,甚至“惟一”。中国新闻出版界乃至文学艺术界,不说走向世界,仅说打入美国,单凭葛氏一人,显然杯水车薪。美国大兵葛氏能借驻军台湾苦学汉语,靠译萧红起家;你泱泱大国、芸芸众生、莘莘学子中真出不了个靠汉译英吃饭的后生吗?本文拉杂地记录的这不是新闻的新闻,更为及早能出个译萧红及其他的学人优势所在鼓与呼!
这里要问,美国现政府那样地去中国化、甚至不惜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当口儿,多一些比国人毫不逊色地研究萧红的学者兼翻译家,有关“过誉”之说,不显得“过冷”了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