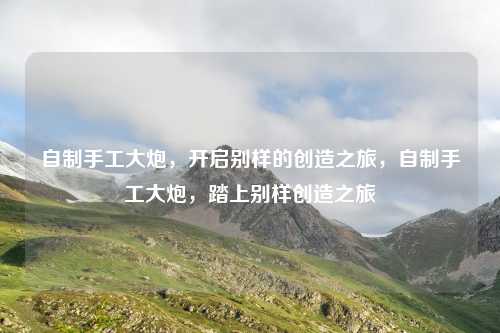慰安妇是什么,南京遇难纪念馆三个展区在一块吗
慰安妇是什么,南京遇难纪念馆三个展区在一块吗?
不在一起。
南京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中的三个展区,分为南京大屠杀史展区、“三个必胜”专题展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三个展区位置和流线不同,不是连在一起的。

如何看文在寅元月四日邀请慰安妇共进午餐?
南倭本来就不应该签所谓的慰安妇协议的,倭奴国又没进行真诚道歉和政府赔偿,只进行了勉强的由企业出面一般性赔偿而已。所以朴老妪觉得这没错。结果就是此一纸协议要了朴老妪的政治生命!
你认为日本是保守的国家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保守是指哪一方面?我想大概不是指政治方面吧,恐怕着眼点在社会风俗上吧?我试着回答一下。
日本最早的史书是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我手头恰好有一本更早的中国史书《后汉书》,其中《东夷列传》中写到倭国的部分说:“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即在将近两千年前,好像民风还比较淳朴,一个男人娶几个妻子是很常见的现象。
日本的性风俗,据我所看到的文献,主要兴起于江户时代的18世纪初期。性的娱乐,一般只能在陌生人社会中展开,很难想象在一个村落里开一家妓院供村人游乐,大家抬头低头都是熟人,不可能堂而皇之进出这样的地方。17世纪下半叶开始,真正的城市(不仅仅是像平城京平安京这样的王城)开始形成,大量的外来工匠到江户(现在的东京)参加城市建设,各个地方的大名的家属也被作为人质而居住在江户,人口一下子增加到了几十万,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商业和市民阶级,也刺激了各种需求,包括性的需求,于是在江户的吉原、大坂的新町、京都的岛原和长崎的丸山等地逐渐形成了青楼区(日语称之为“游郭”,青楼女子日语叫“游女”),一开始这些青楼美其名曰“茶屋”,好像是喝茶的地方,其实是青楼。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绘画艺术中有一种叫“浮世绘”,这浮世绘中有一个门类叫“美人画”,它的一个旁门就是春画。中国的春画我倒是没怎么看过,《金瓶梅》中有一些插画,好像没有什么,但日本的春画确实尺度相当大,就是男女交媾的画面,且与中国不同,它把男女的性器都画得十分夸张,这样的美术图册,今天的日本有卖。也有专门研究日本性风俗的著作,附有插画。据说游郭兴盛的时候,游人如织。明治以后,洋人来了,见日本人如此开放,一方面趁机寻乐,一方面却指责日本这个国家不文明,居然有如此大规模的公娼。于是明治政府为了要显示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不得不颁布法令,限制公娼,或者表面上取缔了公娼。但事实上,这样的场所一直存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有不少日本女子到海外去做皮肉生意,大多是为生活所迫。日本发动对外战争时,要在军队里了开设所谓的“慰安所”,至今还留下了强征慰安妇的问题。
二战以后,一度沉淀的青楼,又以各种新的形式复活,日本政府为了限制这样的商业活动,也屡屡发布了许多法令,至少在今天,公开卖淫的场所已不被允许,但是准红灯区却是比比皆是,所谓的脱衣舞场、洗浴场、色情酒吧以及性慰藉器商店、性杂志、性录像带等,随处可见,并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性产业,据说,最兴盛的时候,性杂志有五百多种。但是,各种印刷物或录像带等,性器不可正面暴露,各种风俗场里,直接的性交媾不被允许。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确实每天都在频繁发生,因为官方的起诉,必须要有直接的证据,而这样的证据却很难获得。只是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发展的停滞,人们的钱袋缩水,性产业也在逐渐衰败。
顺便讲一下,在街头校园等公共场所,日本男女极少勾肩搭背,男女依偎接吻的场景几乎看不到。据说,在婚前,日本的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婚后则各自约束,出轨的情况并不常见。日本女子的衣着,在公共场合,暴露的也很少,女性穿热裤、吊带衫的没有中国那么多,露脐装也极少见。利用权力进行性骚扰的,全世界都一样会有,但日本自20年前出台了很严格的反性骚扰法和规章,大学里对教师骚扰女生,有极严格的处理,一旦举报成立,往往开除。这是因为,现在的日本社会,法制越来越健全,对女性的保护也做得越来越好。
简单说到这里。
现在日本人很惨吗?
这阵子是不那么惨了,可是也曾经惨过。
60万日军被苏联俘虏,一路北上远东,在荒芜、泼水成冰的西伯利亚做苦力,冻饿、生病而死的多达55000余人。剩余的虽然被遣返回国,不过也折磨的瘦骨嶙峋。
另外在二战后期,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无差别轰炸,也曾经让日本满目疮痍,犹如人间地狱。在日本死不投降的情况下,美国对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一次死伤人数达数十万人。
两个地区被夷为平地,核灾难的幸存者,后半生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很多都因为遭受到核辐射,而患癌而死。
日本政府为了应付美国占领军,使日本女性不遭到日本军队祸害别国那样的同等报复,组织了卖笑的女子和那些自愿为国出力的良家女子,建立大量的类似慰安所之类的风月场所,供美国大兵们发泄欲望。
尽管日本后来因为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国防支出较少,可以专心发展经济而从二战的废墟里实现了经济崛起,但是因为是战败国的关系,军事、经济、政治、外交都没有独立性而受到美国的牵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兴兴向荣,很快跻身世界第二,直望美国项背,日本国内都兴高采烈的做着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梦想,美国却没有让他们如愿。因为战败国的地位,根本就无法坚持自己的发展方略,被美国强迫签下了不平等的广场协议后,日本的经济陷入了停滞,到如今,已经整整失去了相近40年。
这就是做亡国奴的代价,所幸日本是赶上了现代文明社会,要是退回到中世纪,日本早已经亡国灭种。而且,二战的同盟国毕竟是打着打败法西斯,拯救全人类的道德大旗在进行战争,所以基本都坚持了道德底线,否则日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我们假设,是轴心国赢得了战争,题主还会认为亡国奴做的舒服吗?那就看看南京大屠杀、犹太人集中营、苏联的2700多万冤魂吧。
我在霞村的时候故事梗概?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了少女贞贞在日军占领霞村后,被掳去做慰安妇,并利用这层特殊身份为抗日提供线报。回到家后的贞贞遭受了村民的排斥,而另一方面她被抗日分子敬为英雄。丁玲试图通过贞贞“失贞妇女”和“抗日英雄”双重身份的拉扯,探讨贞贞这一普通农妇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下的新出路。
一、反抗包办婚姻,初显贞贞魄力霞村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贞贞是村里刘大妈家长女,因家中无子,所以将女儿的婚事看得尤为重要。贞贞父亲想把她嫁给一个米铺小老板做填房,看重的无非是对方还算殷实的家境。贞贞不肯,她心里已经有了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夏大宝。贞贞性格刚烈,曾说服夏大宝私奔。这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出格的行为。可见,贞贞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有了铺垫。奈何夏大宝出身贫寒,性格也比较懦弱,没有胆量挑战传统权威。贞贞只得去天主教堂找外国神父要做“姑姑”,正是因为这次经历,贞贞错过了逃跑的机会,被日本兵抓去做了一年多的慰安妇。革命的风已经吹到了霞村,但未能彻底吹走村里迂腐守旧的空气,贞贞大胆反抗包办婚姻的魄力,是她扭转命运的生命底色。二、贞贞自我意识的萌芽重新回到霞村的贞贞,面临着一个全然陌生的农村社会。在村民眼里,贞贞是个被日本人占有过的不洁之人,是个败坏了传统妇德的宗族异类。男人们说她是破铜烂铁,女人们则在她身上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她们都是圣洁的。文中有大量笔墨描绘村民们对贞贞直接的语言和道德暴力,他们仿佛形成了一条战线,将她排斥在传统宗法社会之外。再来看贞贞父母,他们将自己视作女儿被抓去当慰安妇事件的受害者,而在无形之中和村民们站在一起,对贞贞施加压力。当夏大宝来求亲时,贞贞父母哭天喊地,试图强迫贞贞同意这门婚事,以挽救他们被败坏的名声。从贞贞母亲这句话,我们看出他们的初衷并不是女儿的幸福,而是为了挽救他们在村里的名声。他们抱怨贞贞不替父母着想,可他们又是否真正为女儿着想过。包括贞贞亲人,如刘二妈一类,他们也不齿于她的经历。面对贞贞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古老的宗法社会呈现其麻木无情的一面。村民们的好奇、鄙夷、不明所以的从众、自以为是的同情以及来自亲人的不理解,皆汇聚成一种多数人的无声暴力,缠绕着刚从日军性暴力中顽强挣脱出来的贞贞。然而另一方面,贞贞成了活动分子口中的英雄。贞贞是个很有生命活力的角色。她第一次正面出现在作者笔下时,并不是一个受尽磨难的悲苦形象,而是一个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心的少女。她请求书中的“我”教她所不知道的知识。即便是身处毫无希望的慰安所,贞贞主动学习日语,为抗日地下间谍工作提供了可能性。从书中的描述来看,贞贞走上这条路有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活着”是贞贞的第一要义。她要自己心肠变硬,活下去,那会的她并没有想去探索另一种活法的可能性。后来,贞贞学会了点日语,开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抗日做贡献,倒是给了她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向。此刻的贞贞更多是一种意识的萌芽,她还没有挣脱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直到夏大宝来求婚,贞贞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三、拒绝求婚,勇敢追求新出路在贞贞被抓去当慰安妇后,夏大宝一直生活在自责中,责怪自己当初没能再大胆点跟贞贞私奔。因此,当贞贞再次回到霞村,夏大宝便上门求亲。他当然知道慰安妇是种什么情况,也知道贞贞染上了脏病,此举不仅是一种赎罪,也能看出夏大宝作为男人的担当。贞贞父母知道女儿这种情况,除了夏大宝,再没有哪个男人会要她,便强迫贞贞同意这门婚事。贞贞不想有个人疼她爱她,抚慰她受伤的身心?她当然想。文中描述在知道夏大宝来提亲时,一贯洒脱明朗的贞贞突然变得烦躁起来。这和平常的贞贞很不一样,说明夏大宝的提亲对贞贞是很有吸引力的。接受夏大宝的提亲意味着她可以借助这桩婚姻重新回到村庄的伦理结构中,重新回到原有社会。所有人,包括“我”都认为这是贞贞修复个人、家庭以及村庄在战争中蒙受的伤害的最好办法。但是贞贞经过一翻斗争后,坚定地拒绝了。当众人派“我”去劝说时看到“贞贞把脸收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得见有两颗狰狞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的样子完全变了,几乎使我不能在她的身上回想起一点点那些曾属于她的洒脱、明朗、愉快,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像一个复仇的女神…“这是笔者第一次看到没有掩盖真实情感的贞贞,她用狰狞的眼睛看着众人,将自己主动划离了原来的社会。她不是不想回到原来的环境,而是她已经回不去。他们的存在将时刻提醒贞贞曾经受过的伤害,而众人的看客表现更是让贞贞对自我和村庄之间有了清醒的认识:她的经历在霞村的伦理结构中和人们的思维惯性中,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理解的。夏大宝也好,她的家人也罢,试图将她再次纳入村庄的正常生活里,然而这种单方面的意愿只会让受害的一方更加压抑。“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这是贞贞和原有社会一次精神上的彻底决裂。于她于夏大宝,更好的生活便是各奔前程。组织准备送贞贞去治病,贞贞也想趁此机会,去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